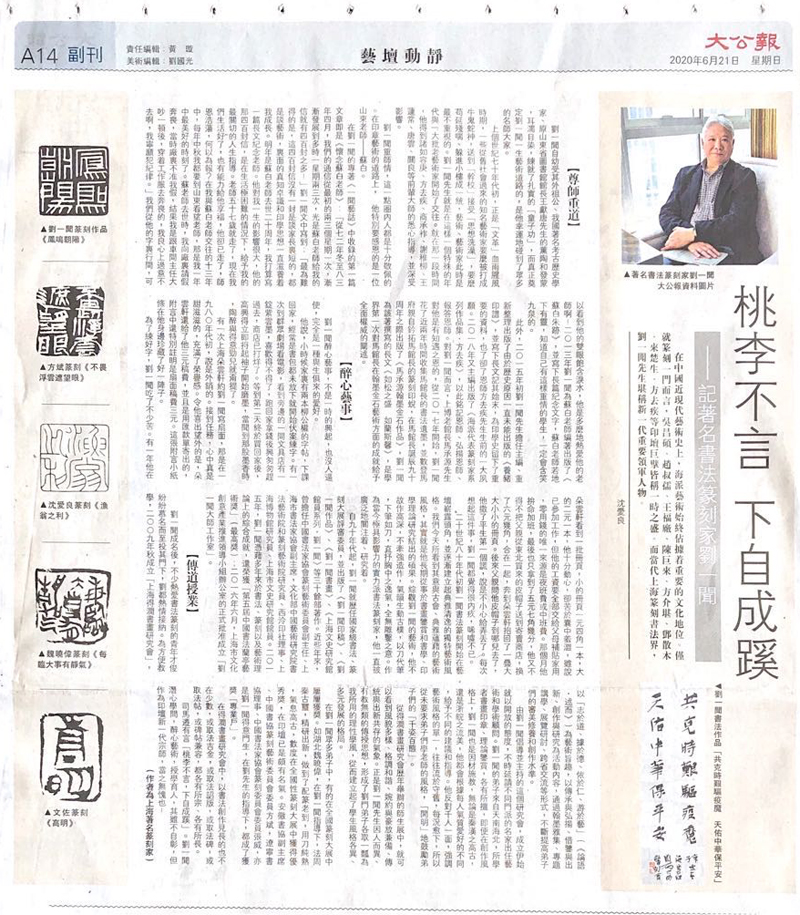|
|
|
评说 |
|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记著名书法篆刻家刘一闻
|
沈爱良
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海派艺术始终佔据着重要的文化地位。仅就篆刻一门而言,吴昌硕、赵叔孺、王福厂、陈巨来、方介堪、邓散木、来楚生、方去疾等印坛巨擘皆称一时之盛。而当代上海篆刻书法界,刘一闻先生堪称新一代重要领军人物。
【尊师重道】 刘一闻自幼受其外祖公、我国著名考古历史学家、原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的薰陶和发蒙,耳濡目染,练就了扎实的“童子功”,而真正奠定刘一闻一生艺术道路的,是他幸运地碰到了众多的名师大家。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正是“文革”血雨腥风时期,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名艺术家要麼被打成牛鬼蛇神,送到“幹校”接受“思想洗澡”,要麼苟延残喘、躲进小楼成一统,艺术、艺术家此时是最不重视的。刘一闻先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与一大批老艺术家开始了交往。就在那一段时间,他得到诸如容庚、方去疾、商承祚、谢稚柳、王蘧常、唐云、关良等前辈大师的悉心指导,并深受影响。 刘一闻重师情,这一点圈内人都是十分敬佩的。在印章艺术的道路上, 他特别要感恩的是一位山东老师│苏白。 在刘一闻的专著《一闻艺话》中收录的第一篇文章即是《怀念苏白老师》:“从七二年冬至八三年四月,我们的通信从最初的两三个星期一次,渐渐发展到多时一星期两三次,光是苏白老师给我的信就有四百封之多!”刘一闻文中写到:“最为难得的是,这四百封信没有一封是谈家长裏短的,都是谈艺术,裏面的真知卓识和印学思想一直滋养着我成长。明年是苏白老师去世二十周年,我打算写一篇长文纪念老师。他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他的那四百封信,是在生活极困难的情况下,给予我的最关切的人生指导。老师五十七岁就走了,现在我们生活好了,也有能力给他享福,他却已走了,师恩浩蕩,何以为报?在我与苏白老师交往的十三年中,每年中秋我都要到山东看望老师,那是我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刻了。苏老师去世时,我向厂裏请假奔丧,当时厂裏不准我假,结果我是跟车间主任大吵一顿后,穿着工作服去奔丧的,我良心上过意不去啊,我宁愿犯纪律。”我们从他的字裏行间,可以看到他的双眼饱含泪水,他是多麼地热爱他的老师啊!二○一三年刘一闻为苏白老师编著出版了《苏白朱迹》,并写下长篇纪念文字,苏白老师若地下有灵,知道自己有这样重情的学生,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此外,二○一五年初刘一闻先生担任主编、重新整理出版了由於历史原因一直未能出版的《养猪印谱》,并写下长文记其始末,为印学史留下了重要的资料,也了却了恩师方去疾先生生前的一大夙愿。二○一八年又主编出版了《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方去疾》,以此铭记恩师、弘扬恩师、报答恩师。对刘一闻而言,上博老馆长马承源先生对他是有知遇之恩的,从二○一七年开始,刘一闻花了近两年时间收集马馆长的书法遗墨,并数登马府亲自钤拓马馆长的篆刻印蜕,在马馆长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出版了《马承源翰墨金石作品》,刘一闻为该著撰写的长文《如松之盛 如兰斯馨》,是学界第一次对马馆长在翰墨金石艺术方面的成就给予全面权威的阐述。
【醉心艺事】 刘一闻醉心艺事,不是一时的兴起,也没人逼使,完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爱好。 他说,小时候家裏有两本柳公权的字帖,下课回家,经常是书包都未放下就开始伏案练字。有一次到群众剧场看电影,看到旁边的一间文具店有一锭紫云墨,喜欢得不得了,跑回家拿钱后兴匆匆赶过去,商店已打烊了。等到第二天终於买回家后,高兴得立即捋起袖子开始磨墨,当闻到那股墨香时,陶醉与得意劲儿就甭提了。 有一次上海朵云轩约刘一闻写扇面,那是在一九八○年代初,说是外销的。接到任务,心中真是甜滋滋的,充满了荣誉感。令他喜出望外的是,朵云轩还给了他三元稿费,并且是用汇款单寄出的,附言中还特别註明是扇面稿费三元。这张附言小纸条在他身边珍藏了好一阵子。 为了练好字,刘一闻吃了不少苦。有一年他在朵云轩看到一批册页,小的册页一元四角一本,大的二元一本,他十分动心,却苦於囊中羞涩,虽说已参加工作,但他的工资要全部交给父母补贴家用,零用钱的唯一来源是夜班费或中班费。那个月他拚命加班,最后也只拿到了五元七角几分,他又不得不把父亲从东北买来的皮帽子送到寄卖商店,换了六元几角,合在一起,奔到朵云轩抱回了一叠大大小小的册页。后来父亲问他皮帽子到哪儿去了,他撒了平生第一个谎,说是不小心给弄丢了。每次想起这件事,刘一闻都觉得很内疚,唏嘘不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刘一闻书法篆刻开始在艺坛崭露头角,并逐渐建立起典雅清逸的独特艺术风格。我们今天所看到其意与古会、典雅蕴藉的艺术风格,其实就是他长期从事於书画鉴赏和书学、印学理论研究结出的硕果。综观刘一闻的艺术,他不故作高深,不牵强造作,气韵生动古樸,以刀代笔,下笔如刀,直抒胸中之逸气,全无雕凿之意。作为当今极具影响力的实力派书法篆刻家,他一直被广泛地关注着、研究着。 自九十年代起,刘一闻就历任国家级书法、篆刻大展评审委员,并出版了《刘一闻印稿》、《刘一闻作品》、《刘一闻书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系列.刘一闻》等三十余部著作。近些年来,曾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艺术院和篆刻艺术院研究员、西泠印社理事、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二○一五年,刘一闻凭藉多年来於书法、篆刻以及艺术理论上的综合成就,还荣获“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艺术奖”(最高奖);二○一六年六月,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正式批准成立“刘一闻大师工作室”。
【传道授业】 刘一闻成名后,不少热爱书法篆刻的青年才俊纷纷慕名而至投其门下,刘都热情接纳。为方便教学,二○○九年秋成立“上海得涧书画研究会”,以“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论语.述而》)为艺术旨趣,以传承与弘扬、借鉴与出新、创作与研究为活动内容,通过翰墨雅集、专题讲学、展览研讨、跨省交流等形式,不断提高弟子们的审美修养和创作水準。 由刘一闻倡导并主持的这个研究会,成立伊始就以开放的态度,不时延请不同门派的名家出任艺术和学术顾问。刘一闻的弟子来自天南海北,所学者书画印章、理论鉴赏,各有所擅,即便在创作风格上,刘一闻也是因材施教,无论是秦汉之高古,还是浙皖之流美,他都会根据每人气质爱好的不同,给予不同的建议和指导。他反对千人一面,强调艺术风格的单一,往往流於守旧,每况愈下,所以从未要求弟子们学老师的风格,“开明”地鼓励弟子们的“千姿百态”。 从得涧书画研究会历年举办的师生展中,就可以看到风貌多样、格调和谐、婉约与豪放兼备、传统与出新共存的气象。正是刘一闻先生因人而异、有教无类的传授思想,形成了刘门弟子各取一瓢为我所用的理性学风,从而建立起了学生风格各异、多元发展的格局。 在刘一闻众多弟子中,有的在全国篆刻大展中屡屡获奖。如湖北魏晓伟,在刘一闻指导下,法周秦古玺,精研出新,做到了配篆老到,用刀纯熟,气息高古,数度在全国性篆刻大展中获得优秀奖,在印坛已是颇有名气。安徽书协副主席、中国书协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方斌,辽宁书协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张威,亦是刘一闻得意门生,在刘先生的指导下,都成了获奖“专业户”。 在得涧书画研究会中,以书法创作见长的也不在少数,或取法吉金,或取法诏版,或取法碑,或取法帖,或碑帖兼容,都各有所宗、各有所长。 司马迁有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刘一闻潜心学问,醉心艺术,授学育人,其虽不自彰,但作为印坛新一代宗师,当之无愧也!
(作者为上海著名篆刻家) (刊登于2020年6月21日《大公报》第A14版。链接:大公网)
2020年6月21日《大公报》
刘一闻
(若斋整理) |